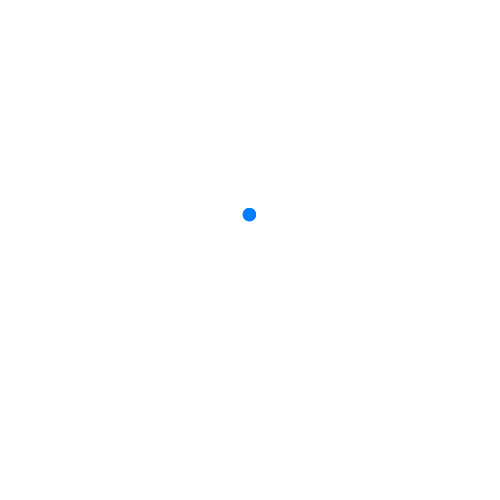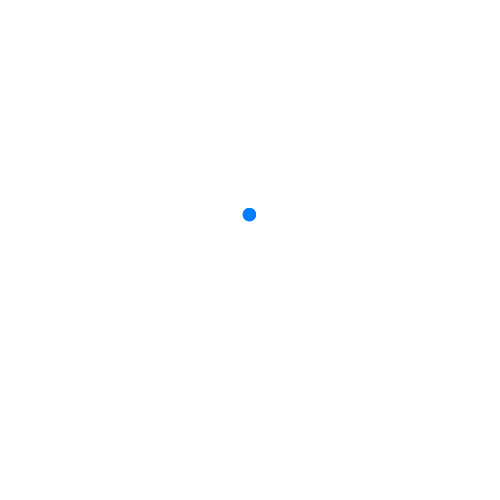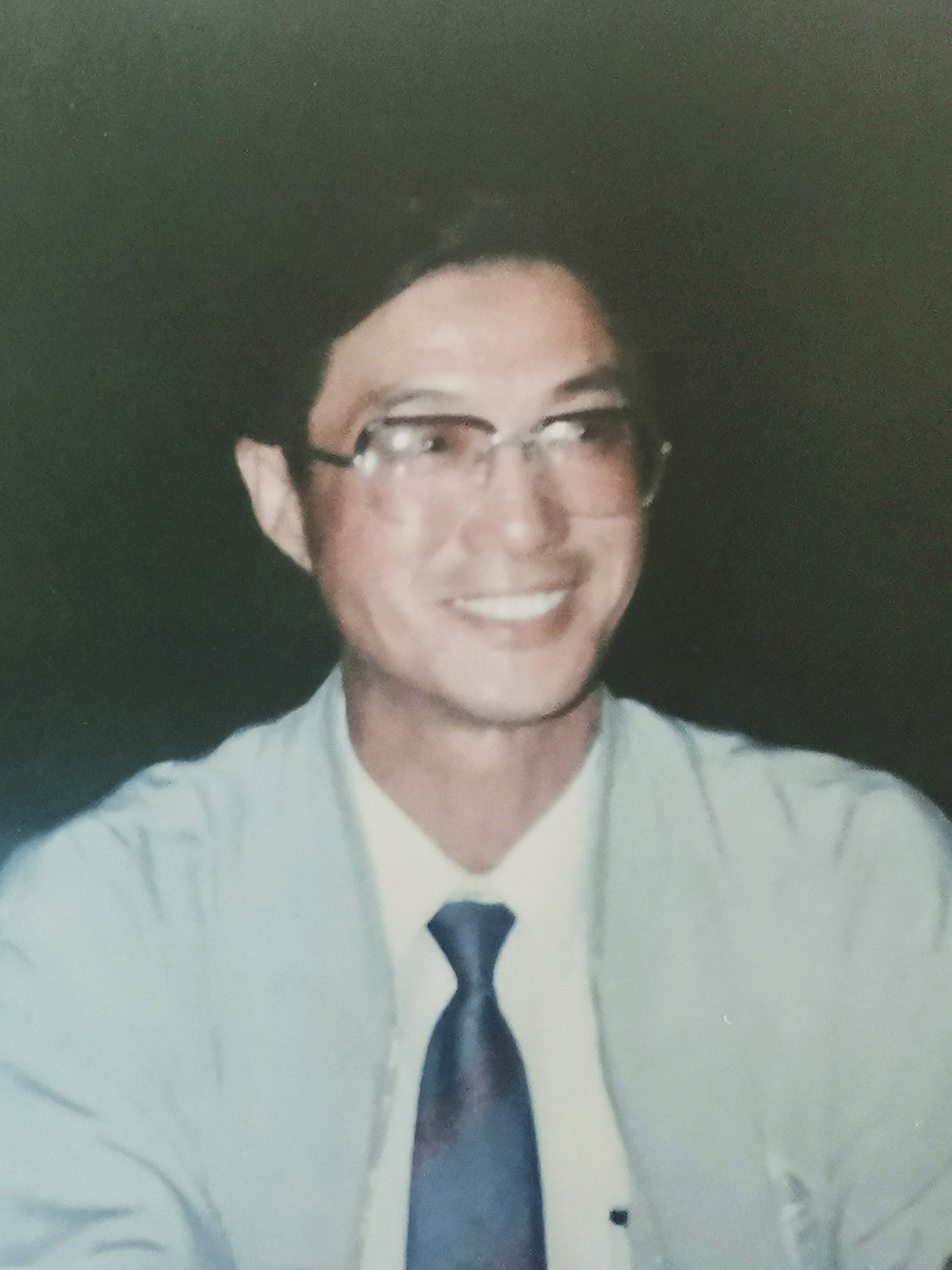杜旭生平事迹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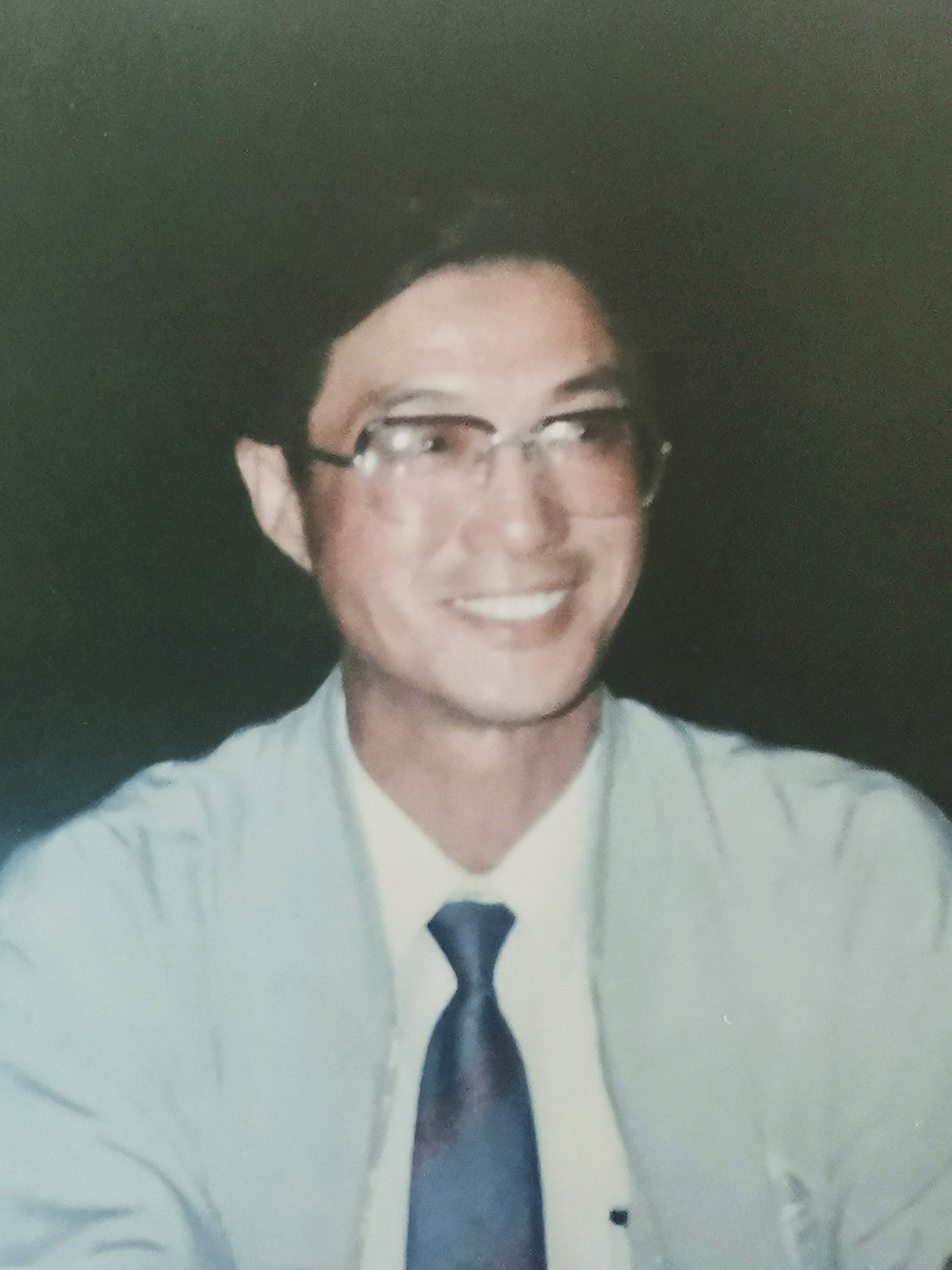
杜旭生平简介:
父亲生于1944年6月21日,农历甲申年五月初一,时逢夏至,这是我根据墓碑上的日期用万年历查到的;他卒于1996年11月10日,农历丙子年九月三十,次日便是“寒衣节”。我对父亲生平所知甚少,原因之一是始终聚少离多,累计和他共同生活的时间也就6年;原因之二是他走得太突然,年仅52岁,正值盛年,远没到含饴弄孙回首往事讲述光荣历史的年龄。我只能从自身经历和零星听长辈、亲故的对谈中,对他的生平略有所知。
对于父亲早年的成长经历,我所知近乎零,很后悔祖母健在时没多跟她聊聊。依稀知道因前面有几个孩子没立住,他成为家中长子,也因此备受祖父母的宠爱。其实家中条件十分有限,而且家教很严。祖父宝祥公(1918-2007)是普通的铁路工人、工段班长,祖母(1923-2015)没有工作。尽管土改时因曾祖向阳公(1892-1963)曾收留一名刘姓逃难者“以工换粮”,家庭成分遂被定为所谓“富农”,但是充其量只是勉强解决温饱的水平。祖父自幼失学,自己的名字都写不来,祖母倒是读过几年书,好像是高小毕业。向阳公曾读过四年私塾,思想开明,对长孙的教育自然也很重视。
父亲谱名讳德勤,出生于扎兰屯,3岁时随祖父迁至博克图,于是读书、成家、生子,都在博克图(现属内蒙,当时属黑龙江)。他自幼聪敏过人,行事果敢干练,读书后自己改名杜旭,还自作主张把我叔父杜德俭改名杜彦,可知他年轻时就是很有主见之人。中学毕业后,可能因祖父、叔祖都在铁路工作的影响,他没有考大学,而是考入满洲里铁路专科学校,毕业后即进入铁路工程局,这使得他的学历仅止于中专,到后来只重文凭的时代,对于他的发展颇有些影响。
对父亲最早的记忆非常模糊,因为我的整个童年,他都在非洲援建坦赞铁路。坦赞铁路是一条贯通东非和中南非的交通大干线,东起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,西迄赞比亚中部的卡皮里姆波希,全长1860.5公里。1970年10月26日动工,1975年6月7日全线铺通,同年10月23日全面建成并试运营。1976年7月建成通车,14日正式移交给坦、赞两国政府。是东非交通动脉,也是迄今中国最大的援外成套项目之一。父亲从1970-1975年参与了坦赞铁路修建的全过程。他是摄影爱好者,留下不少珍贵照片。
关于父亲的工作,我所知甚少。小时候刚到榆次,印象中同事多称呼他“杜技”,那时他的职称是“技术员”,这是很初级的技术职称。他供职于铁三局五处机械科,科长沈德昌伯伯不知健在否?依稀记得沈家女儿和姐姐同班。后来,在我上初一时,父亲晋升为“助理工程师”,英文课刚好讲到“engineer”,我请教甄建丽老师,于是知道了assistant engineer。这次翻检遗物,看到他的工程师资格证,那是1987年,我已升入高三。九十年代初他终于晋升为高级工程师,这是对他业务能力的认可,可惜不知证书放在何处。大约在1985年,父亲晋升为五处机械科科长,1989年改制,机械科更名为“机械装备经租部”,于是乎他这个科长一跃而成为“部长”,他自己和同事们也常常以此调侃这次改制,不久好像真的又改回去了。
大概是从1990年开始,父亲已是五处的副总工程师,一度投身于京九铁路前期开工准备工作,身份是铁三局五处京九项目指挥部副总指挥。指挥部设在河北固安,好像是1991中秋节?母亲和姐姐从山西到固安陪他过节,约好时间后,我从北京坐长途汽车过来汇合,这是我唯一一次陪父亲在工地现场过节。从清华出发,辗转换乘,颠簸了数小时终于抵达固安,指挥部就在国道旁边的一个院子,条件非常简陋。记得当时正是项目征地谈判的关键时期,父亲为此颇为操劳。
京九铁路是连接北京与香港九龙的重大铁路工程,当时是国内投资最多、一次性建成的最长双线铁路,其投资仅次于长江三峡水电工程。1992年,开工筹备工作基本就绪,预见到对架桥铺轨机的需求将会猛增,父亲受命出任铁三局邯郸机械厂厂长,主持技术攻关,生产新型大跨度架桥铺轨机。我当时正好在河北邢台钢铁厂做毕业设计,开展“八五”攻关课题焦化废水生化降解技术研发。于是,两次利用周末从邢台到邯郸探视,对他的厂子还留有些许印象。
父亲重视工厂的文化建设,到任不久就发起了首届艺术节、组织召开职工代表大会,并且顺利推进企业改制,完成全员合同签字工作,现在看来,父亲还是颇具现代企业家精神的。当然,企业的生命在于核心技术,为此父亲积极推动与欧洲知名企业的合作,主持新型架桥铺轨机技术革新项目。终于,在1993年京九铁路全线开工前,技术革新获得成功,“长征III型架桥铺轨机”及时、顺利交付使用,有力保障了京九铁路工程建设。1994年又在北京西客站项目良乡段发挥关键作用。
1994年,父亲不辱使命,邯郸机械厂顺利完成技术革新,生产走上正轨,主打产品“长征III型架桥铺轨机〞源源不断地投入工程一线。这时,他再次接受挑战,出任铁三局长治北水泥厂厂长。此时水泥厂管理混乱,工艺落后,生产经营举步维艰、困难重重,面临着生产工艺革新改造的巨大压力。父亲从一位机械工程师要转型为水泥生产管理者,其挑战显而易见。年逾半百的他再次进入战斗状态,整顿管理秩序、了解工艺前沿、申请国家技改立项……一点点把一个濒临破产的厂子带入现代企业治理轨道。正当胜利在望之时,他却因一场意外蘧然而逝。
父亲自幼聪慧,待人赤诚,他的朋友遍及三教九流,在我的印象里,只要他在家,晚上总是高朋满座、烟雾缭绕。他从中专毕业后即孜孜不倦地投身中国铁路事业,从东北到陕西、再到山西;从坦赞铁路、胶济复线,再到京九铁路;从技术员、助理工程师、工程师,到高级工程师;从普通科员、到技术科长、总工,再到铁三局邯郸机械厂厂长、长治水泥厂厂长。他的短暂一生,是不断迁徙、不断奔波的一生,也是不断进取、积极奋进的一生。常年的工程现场风吹日晒,令他的皮肤总是那么黝黑,发着古铜色光芒。
他兴趣广泛,聪敏好学,心灵手巧,从家具设计、制作,居室装修、房屋修缮,到公路铁路工程建设;从手表闹钟缝纫机维修,到摩托车汽车卡车原理及操控;从篮球排球乒乓球,到唱歌跳舞下棋打牌;举凡各种文体活动、各种必须的业务知识,他都积极学习、广泛涉猎。特别是1994年调任水泥厂后,他从头学习水泥生产工艺,致力于生产线升级改造,并且曾和我讨论水泥厂废水处理及环境影响等问题。正当水泥行业大势上扬,而他麾下的水泥厂提升改造工程顺利推进之时,一场意外让他充满活力与干劲儿的生命永远定格在52岁。
今年,我已52岁。我常常在体育运动时想到父亲,他那时的身体机能应该和此刻的我相差无几吧,他如果活着,也就刚满78周岁,以现在的医疗水平和生活条件,应该依然健康而有活力吧。然而,又如何?我们永远无法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一个先来,我们唯一可以把握的就是当下,珍惜当下,珍惜自己,珍惜身边的亲人友人,这是我作为一名父亲,在失去父亲26年后的父亲节,发出的些许感慨。
谨以此文作为我对父亲的特别纪念。
幼子:杜鹏飞